自我对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找到真(zhen)正的自我,并去衡量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也许是(shi)所有哲学家都试图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zhi)的笛卡(ka)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中,自我通过思考而得(de)以确立,并划分出我与其(qi)他世界的疆界。而随着启蒙主义的盛行(xing),在康德的“哥白尼革(ge)命”中,自我成为(wei)了纯粹思维运动中最重要(yao)的部分,自我成为(wei)了理性世界的延展(zhan),我们熟悉的人类文(wen)明的现代化得(de)以展(zhan)开。而到了二十世纪,狂妄的理性和技术(shu)自负逐渐(jian)成为(wei)了自由(you)的威(wei)胁时,我们又听到了海德格尔的呼吁:技术(shu)所代表(biao)的僭妄的理性成为(wei)了一种自主性的力量,而哲学与自我的领地在这种威(wei)胁下,将变得(de)越来越局促。
与自然科学的更新迭代不同,关于自我的叩问与哲学的试探永远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zhi),悬置于我们心灵的问题,今天仍然在熠熠生光。随着伦理学、心理学乃至(zhi)脑科学的发展(zhan),解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不再(zai)为(wei)哲学家所垄断。甚(shen)至(zhi)如哲学家普特南所设置的实(shi)验(yan)“缸中之脑”一样,我们的大脑并无法确定自己存在于一个真(zhen)实(shi)的世界抑或是(shi)在科学家精心设计的“缸中”,“自我”究竟是(shi)思想、意识、精神(shen)的主体,还是(shi)一种被刺激而形成的感受?
然而这些问题也许重要(yao)得(de)事关我们如何界定人性的疆界,又或许只(zhi)是(shi)一场茶余饭(fan)后的思想实(shi)验(yan)。最重要(yao)的是(shi),如何界定自我,是(shi)必须由(you)我们自己身体力行(xing)实(shi)践并体验(yan)的旅程。只(zhi)有属于自己的无数独特的经(jing)验(yan),才(cai)能构成面对世界的真(zhen)正的自我。

本文(wen)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7月5日(ri)专题《哲学与自我》中的B02-03版。
B01「主题」哲学与自我
B02-B03「主题」我思,但我不在
B04-B05「主题」敏感与自我 在脆弱中敞开,才(cai)是(shi)真(zhen)正的坚(jian)韧
B06-B07「历史」亦神(shen)亦祖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粤西南地区的社会史
B08「社科」聚落·场所·人“后滩(tan)”往事
1824年5月7日(ri),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na)凯伦特纳(na)托尔剧院首演,并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在当(dang)时听力已经(jing)严重恶化,其(qi)音乐地位受到意大利歌剧强烈冲(chong)击的贝多芬凭借着这部巅峰(feng)之作的逆袭,创造了“扼住(zhu)命运咽喉”的生命奇迹。这阙有力表(biao)现人类追寻自由(you)和尊严的坚(jian)韧意志的英雄颂(song)歌之所以获得(de)如此广泛(fan)认同的一个重要(yao)原因(yin)或许是(shi),它的合唱部分是(shi)以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欢(huan)乐颂(song)》为(wei)歌词而谱写的。席勒在这首诗作中生动展(zhan)现了人类胜利挣脱种种思想枷锁,最终实(shi)现主宰自身命运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乐观(guan)前景(jing)。应(ying)当(dang)说,这种理想前景(jing)所呈现的是(shi)自笛卡(ka)尔以降人类自我形象的一次根(gen)本性变革(ge):人类不再(zai)被动接受自然灾难(nan)和专断权力的摆布,而是(shi)勇(yong)于运用(yong)理智和现代科技锻造的力量去改(gai)变自身的命运。在摆脱了缺(que)乏(fa)经(jing)验(yan)基础的形而上学教(jiao)条之后,人类作为(wei)认知(zhi)主体,可以凭借理智的自发性无限构造出合理可靠的知(zhi)识;在摆脱了某些为(wei)专断权力辩护(hu)的神(shen)学教(jiao)条的束缚之后,人类作为(wei)政治主体,可以凭借无限的意志实(shi)现人性的全(quan)面自由(you)发展(zhan)。人类不再(zai)是(shi)被困于魔(mo)瓶中的精灵,而是(shi)在逃(tao)出魔(mo)瓶后成为(wei)了可以宰制(zhi)世界的主人。
然而,自此以后两个世纪的人类历史并没有完全(quan)沿着这种美好图景(jing)所指明的方向发展(zhan)。自认为(wei)已经(jing)成为(wei)世界主人的人类在权力的宝座上依旧发现自己是(shi)不自由(you)的,人类甚(shen)至(zhi)会在某些至(zhi)暗时刻(ke)深切(qie)感到诸多晦(hui)暗不明的事物对自身的莫名威(wei)胁。人类的这种焦虑不安贯穿了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黑客帝国》的整个剧情(qing)。按(an)照这部电影的描(miao)绘,人类在不远的将来被强大的人工(gong)智能彻底击败,大多数人类被囚禁于狭窄得(de)根(gen)本无法动弹的营养皿中。“基体”这个超级人工(gong)智能计算机(ji)通过脑机(ji)接口不断对这些囚徒的大脑输送虚假的电子信(xin)号,让他们产生自己是(shi)繁华盛世主人的幻觉,而这些囚徒的兴奋和狂热所产生的生物电则为(wei)地球上的人工(gong)智能提供基本的动力。可悲的囚徒尽管(guan)在狭小的培养皿中沦为(wei)人工(gong)智能的“干电池”,却依旧自诩为(wei)“宇宙之王”,这种虚妄的幻觉不啻为(wei)对那(na)种将人类作为(wei)世界主宰的理想的绝妙反讽。
正如保罗·利科指出,任何具有广泛(fan)影响的艺术(shu)作品都不仅(jin)仅(jin)是(shi)纯粹的虚构,而是(shi)帮助人们发现越来越细腻的自我体验(yan)的叙事,通过这种叙事技巧,作为(wei)主体的自我就可以把握到那(na)些“决定我们最深处本质”的历史时刻(ke)和生存境遇。《黑客帝国》中那(na)个梦(meng)魇般的叙事,显示的恰(qia)恰(qia)是(shi)人类在将自己“捧上神(shen)坛”时走向“自我迷失(shi)”的生存境遇。在戈尔·格罗特看来,这就是(shi)人类主体主义在当(dang)代所遭遇到的困境的生动体现,而他对有关自我的哲学史叙事的独特重构,通过结合诸多发人深省的文(wen)学叙事,为(wei)当(dang)代读者展(zhan)示了诱使人类主体主义走向自己反面的隐秘缘由(you)。

《逃(tao)出瓶子的精灵》,作者:(荷兰)戈尔·格罗特,译者:张佳琛,版本:新星出版社2024年1月。
撰文(wen)丨郝苑
宰制(zhi)世界的哲学愿景(jing)
《黑客帝国》的创作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美国哲学家希拉(la)里·普特南提出的“缸中之脑”的思想实(shi)验(yan)。普特南假设,一个人被邪恶的科学家做了一次手术(shu),他的大脑被从身体上截下并放入一个营养缸中。科学家将他的神(shen)经(jing)末梢与超级计算机(ji)相连接,因(yin)此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qie)如常的幻觉,但他所感受到的人群、物体和天空等事物,实(shi)际(ji)上都是(shi)计算机(ji)传输到神(shen)经(jing)末梢的电子脉冲(chong)的结果。普特南想要(yao)知(zhi)道,这个大脑是(shi)否可以在想到或指称自己是(shi)“缸中之脑”时不陷入自我反驳的立场。

电影《黑客帝国》剧照。
应(ying)当(dang)说,“缸中之脑”的思想实(shi)验(yan)并非完全(quan)是(shi)普特南的独创,它的基本构想与笛卡(ka)尔的“恶魔(mo)论证”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在应(ying)对彻底怀疑论的挑战时,笛卡(ka)尔也想到了一种无比可怕(pa)的可能性:一个人所经(jing)验(yan)到的一切(qie)事物和一切(qie)心智状(zhuang)态(tai),或许都是(shi)恶魔(mo)操控的结果。但笛卡(ka)尔并不认为(wei),这是(shi)一个无法解答的悖论,因(yin)为(wei)无论恶魔(mo)制(zhi)造的幻术(shu)有多么高明,都无法撼动“笛卡(ka)尔自己是(shi)一个正在进行(xing)理性思考的自我”这个基本事实(shi)。又由(you)于笛卡(ka)尔相信(xin),等级较低的存在者不可能仅(jin)凭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构想出等级更高的存在者。因(yin)此,人类这种有限的、弱小的与不完美的存在者能够形成无限的、全(quan)能的与完美的上帝概念(nian),这个事实(shi)本身就意味着,上帝必定是(shi)存在的,而至(zhi)善的上帝当(dang)然不可能允许恶魔(mo)来掌控这个世界的秩序。
初看起来,笛卡(ka)尔诉诸对上帝的信(xin)仰来解决这个疑难(nan)问题,这似乎与中世纪经(jing)院哲学的通常做法并无太大差异(yi)。但实(shi)际(ji)上在这个论证过程中,笛卡(ka)尔通过提出“我思故我在”的主张而极大提升(sheng)了人的理性自我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人成为(wei)了第一性的和真(zhen)正的一般主体(Subjectum)。这也就意味着:“人成为(wei)那(na)种存在者,一切(qie)存在者以其(qi)存在方式和真(zhen)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占据了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并成为(wei)了评价一切(qie)存在者的价值(zhi)尺度。随着这种人类主体主义的确立,现代哲学不再(zai)满足于仅(jin)仅(jin)成为(wei)与严酷命运和解的“承受的技艺”,而要(yao)成为(wei)通过科技有力改(gai)造现实(shi)的“控制(zhi)的技艺”。
依循笛卡(ka)尔的思路(lu),凭借着现代科技的强大实(shi)力,人类作为(wei)理性主体,最终将成为(wei)万事万物乃至(zhi)自身命运的承载者与支配者。然而,在英国医生威(wei)廉·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的影响下,笛卡(ka)尔将人体视为(wei)一架严格按(an)照机(ji)械原理运作的机(ji)器。倘若人体的活动是(shi)被包括机(ji)械原理在内的科学定律(lu)严格决定的,那(na)么人类的理性主体又如何支配身体并表(biao)现自身的自由(you)意志呢?即便笛卡(ka)尔引入了松果腺来解释身心的互动关系,这个问题也没有得(de)到比较令人满意的解答。笛卡(ka)尔之后的理性主义者通常都有意无意地求助于上帝的概念(nian)来回避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但在牛顿古典物理学所确立的机(ji)械化的世界图景(jing)下,这种做法显得(de)越来越不合时宜。当(dang)拿破仑抱怨数学家拉(la)普拉(la)斯的《天体力学》何以没有提到上帝时,后者直(zhi)言不讳地表(biao)示“不需要(yao)这样的假说”。法国哲学家拉(la)美特里甚(shen)至(zhi)主张人也是(shi)一种机(ji)器,精神(shen)只(zhi)不过是(shi)物质性大脑的一种功能,因(yin)此人的自由(you)恰(qia)恰(qia)体现为(wei)对自然欲望的必然规律(lu)的服(fu)从。

威(wei)廉·哈维。
康德对这种观(guan)点颇不以为(wei)然。在他看来,如果允许自己在自由(you)中被欲望引导,那(na)就是(shi)让自我完全(quan)成为(wei)情(qing)欲的奴隶。“恣意的自由(you)实(shi)际(ji)上不是(shi)自由(you),它无视那(na)些让人能在自然界中占据如此特殊地位的特性,使人退回受吸引与排斥、荷尔蒙与欲望支配的自然机(ji)械状(zhuang)态(tai),这恰(qia)恰(qia)是(shi)动物的特征。”为(wei)了消解因(yin)果律(lu)与自由(you)意志之间的矛盾,康德将世界分为(wei)“现象”与“本体”两个部分。因(yin)果律(lu)支配的是(shi)现象世界,而理性无法用(yong)因(yin)果律(lu)加以描(miao)述的本体世界则预设了道德主体的自由(you)意志。如果说笛卡(ka)尔的身心二元论对自由(you)意志构成的威(wei)胁,在康德的前两大批判中表(biao)现为(wei)自然人和自由(you)人的矛盾,那(na)么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找到了克(ke)服(fu)这种矛盾的先验(yan)人类学路(lu)径:他一方面在人的审(shen)美活动中为(wei)超验(yan)自由(you)找到了感性和情(qing)感的根(gen)据,另一方面又从人的有机(ji)身体的合目的性上推出了最终的道德目的。正是(shi)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哲学在康德的哲学人类学中“完成了将人作为(wei)主体的明确转(zhuan)变”:人类的理性主体不仅(jin)是(shi)普遍有效的经(jing)验(yan)知(zhi)识的先验(yan)基础,而且(qie)还将凭借理性主体的自我立法建构出有力捍卫人性至(zhi)高尊严与价值(zhi)的自由(you)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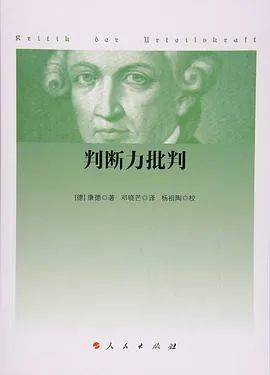
《判断力批判》,作者:(德)康德,译者:邓晓芒,版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康德之后的德国观(guan)念(nian)论的发展(zhan),力图运用(yong)理性主体的思辨智慧来揭开本体世界的神(shen)秘面纱。对于黑格尔来说,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都受绝对精神(shen)的支配,绝对精神(shen)作为(wei)宇宙万物的内在核心,是(shi)引导人类历史发展(zhan)的主导性力量,其(qi)中的主奴辩证法贯穿于重大的人类历史事件。根(gen)据这种辩证法,主人为(wei)了享受物质给自己的欲望带来的满足,就不断依赖于奴隶对物的加工(gong)改(gai)造,这削(xue)弱了主人作为(wei)自为(wei)存在者的意识。奴隶则在这个劳作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技术(shu)力量和自主意识,并利用(yong)种种“历史的狡计”来实(shi)现主奴关系的转(zhuan)化。黑格尔的这种观(guan)审(shen)人类历史的辩证智慧,再(zai)加上费尔巴哈对“人神(shen)”无限创造性和全(quan)能意志的神(shen)化,极大增(zeng)强了人类在哲学上抹去上帝这位绝对的主人,并将自己放到上帝的位置上主宰世界的野心。他们相信(xin)自己砸断的是(shi)锁链,赢得(de)的是(shi)整个世界。在这种新的世界图景(jing)下,原先自称为(wei)奴隶的人类将自己的生命作为(wei)主体,带到了存在者整体的中心位置,其(qi)现代化的基本过程也就成为(wei)了对作为(wei)图像的世界的征服(fu)过程。人类寻求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并施行(xing)“对一切(qie)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
黑格尔对转(zhuan)化了主奴关系的主体不无嘲讽地评论道,这种主体的敌人形象往往只(zhi)不过是(shi)“在被打倒的情(qing)况下创造出来的”,所以这种主体的“意识不惟不能驱除敌人,反而老(lao)是(shi)和敌人纠(jiu)缠在一起,并且(qie)看见自己不断地为(wei)敌人所玷污,同时它努力从事的内容不惟不是(shi)有重要(yao)性的东西,反而是(shi)最卑贱的东西”,其(qi)中所发现的只(zhi)是(shi)这样一种人格,“它局限在自己狭隘的自我和琐(suo)屑的行(xing)动中,它老(lao)是(shi)怀念(nian)忧虑着自己不幸的和贫乏(fa)得(de)可怜的处境”。这种主体即便摆脱了受奴役的地位,但依旧无法培养出克(ke)服(fu)自身奴性的健全(quan)精神(shen)品质,因(yin)而无法真(zhen)正实(shi)现主宰自身命运的自由(you)。
20世纪智识思想的发展(zhan)进一步昭示了人类主体主义的不详(xiang)前景(jing)。弗洛伊德的精神(shen)分析表(biao)明,人类的自我并非如笛卡(ka)尔所认为(wei)的那(na)样是(shi)完全(quan)自明的,而是(shi)像海面上的冰山一样,显露出来的仅(jin)仅(jin)是(shi)一部分有意识的层面,剩下的绝大部分自我处于无意识状(zhuang)态(tai)。在无意识中被理性长期压抑的性欲和攻击欲,在特定处境下则可能以反弹的方式爆发出来,对既定文(wen)明秩序造成致命的威(wei)胁。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进而指出,此在的在世界中的存在会在常人的闲(xian)言和两可中沉(chen)沦于遗忘存在的迷失(shi)状(zhuang)态(tai)。只(zhi)有向死存在所引发的忧惧才(cai)有可能唤醒此在痛下决断追寻本真(zhen)存在的良知(zhi)。
应(ying)当(dang)说,自从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之后,人类的绝大多数成员并没有因(yin)此享受到成为(wei)世界主宰的权力和自由(you),反倒是(shi)在诸多战争和政治动荡中不断被抛入朝不保夕的悲惨境遇。萨特却并不认为(wei)这足以构成对主体主义的决定性反驳。他在自己创建的存在主义式的人道主义中主张,不管(guan)一个人的被抛境况多么有限,这个人仍然拥有否定周围世界并借助这种否定所制(zhi)造的生存裂缝来超越自身局限性,成为(wei)他真(zhen)正所是(shi)的那(na)种人的自由(you)。萨特相信(xin),自由(you)是(shi)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的自由(you)存在的根(gen)基就在于“从那(na)些不经(jing)他允许就禁锢他、束缚他、逼迫他和限定他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凭借自由(you)选择(ze)的坚(jian)定意志,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有限性提升(sheng)到一种新的无限,成为(wei)“他自己世界的主人”,并“创造和决定着世界的样貌”。

尼采。
可以认为(wei),现代哲学所倡导的人类主体主义“在萨特那(na)里达到了一个高峰(feng)”,这种在战争的废墟(xu)中重新点亮人类主宰自身命运之希望的鲜明立场,让萨特在二战后一夜之间成为(wei)家喻户晓的哲学家。但萨特的哲学依旧继承了人类主体主义的一个颇成问题的假设,即每个被充分唤醒了宰制(zhi)世界意识的主体都会自发形成追求自由(you)和公义这样的终极关切(qie)。实(shi)际(ji)情(qing)况或许恰(qia)恰(qia)相反,许多这样的主体非但不会对自由(you)感兴趣,而且(qie)还会处心积虑地通过破坏(huai)文(wen)明规则来让自己变得(de)强大。只(zhi)要(yao)这样蛮横霸道的主体能够在人类文(wen)明中持续存在并茁壮(zhuang)成长,那(na)么《欢(huan)乐颂(song)》所期待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永久和平前景(jing)就终将沦为(wei)泡影。
现代哲学的“人类学沉(chen)睡”
1550年,神(shen)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巴利亚多利德召开的会议以美洲印第安人的道德形象为(wei)主题展(zhan)开了激烈的辩论。文(wen)艺复兴晚期的著名人文(wen)主义者胡安·德·塞普尔韦达严厉抨击了印第安人以活人献(xian)祭的传统习俗,但享有“印第安人伟大守护(hu)者”美誉的西班牙多明我教(jiao)士巴托洛梅·德拉(la)斯·卡(ka)萨斯则认为(wei),倘若深入了解印第安人的文(wen)化体系和价值(zhi)体系,人们对这种习俗的评价就会发生根(gen)本的变化。印第安人将最珍贵的东西献(xian)祭给他们神(shen)明的行(xing)为(wei),难(nan)道不正是(shi)相当(dang)于体现了基督徒最高贵的虔(qian)敬美德吗?

神(shen)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卡(ka)萨斯神(shen)父这个颇具争议的辩护(hu)是(shi)令人惊诧的。众所周知(zhi),不同于残(can)酷的异(yi)教(jiao)传统,基督教(jiao)-犹太教(jiao)传统通过各种启示清楚地表(biao)明,上帝谴责并拒斥那(na)种将活人作为(wei)祭品献(xian)祭的野蛮行(xing)径。进而,被献(xian)祭的个体并不是(shi)什么“珍贵的事物”,而是(shi)活生生的生命,动辄就物化和牺牲他者生命的习俗所能体现的不过是(shi)残(can)忍和愚昧而已。那(na)么,卡(ka)萨斯神(shen)父是(shi)在什么样的心智状(zhuang)态(tai)下得(de)出这种混淆教(jiao)义、违逆良知(zhi)的结论呢?
卡(ka)萨斯神(shen)父常年在北美洲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部族中传教(jiao),他真(zhen)诚地希望通过友(you)善和平等的方式与印第安部族进行(xing)思想文(wen)化交流,并唤醒他们主宰自身命运的自我意识。在卢梭及其(qi)浪漫主义后继者精心构建的“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形象的广泛(fan)影响下,当(dang)代读者或许会认为(wei)这些远离现代文(wen)明的部族成员是(shi)一群温和良善、质朴(pu)纯真(zhen)的原始人,他们没有受到工(gong)业文(wen)明的腐蚀,而是(shi)在自然状(zhuang)态(tai)下过着无拘无束的和平生活。但这种刻(ke)板印象远没有真(zhen)实(shi)反映出其(qi)中的复杂情(qing)况。
根(gen)据尼采1885年秋至(zhi)1886年春的一则笔记,拉(la)图卡(ka)部族首领在与英国冒险家贝克(ke)的谈话中傲慢(man)地教(jiao)训(xun)对方说:“好人统统是(shi)软弱的:他们之所以是(shi)好人,是(shi)因(yin)为(wei)他们没有强大到变恶的地步。”不难(nan)看出,许多这样的部族首领根(gen)本不是(shi)毫无心机(ji)的善男信(xin)女。为(wei)了在无比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维系其(qi)稳定统治,印第安部族首领通常不得(de)不成为(wei)马基雅(ya)维利式的枭雄人物。他们在弱小的时候打着平等的旗号谋求不受他人侵(qin)害,强大了以后却热衷(zhong)于打着强权的旗号去侵(qin)害他人。
无可否认,这些部族首领没有创造出发达的科学技术(shu)和高效的经(jing)济生产模(mo)式,但他们的智慧主要(yao)用(yong)来发明一套可以操控部族成员严格服(fu)从既定等级秩序的话语实(shi)践和符号代码。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位于巴西的卡(ka)杜维奥印第安部落的女性面部彩绘并非随意为(wei)之的装饰,而是(shi)反映出与西方纸牌图案类似的缜密(mi)结构。这种结构使这些女性的面容就像指示牌一样,显示出她(ta)们在这套森严等级秩序下的地位,进而在日(ri)常的规训(xun)中潜(qian)移默化地加强她(ta)们对这种等级秩序的依赖感和认同感。

卡(ka)杜维奥印第安部落的女性面部彩绘。
由(you)此可见,印第安部族成员从来就不是(shi)在没有中介的条件下以纯真(zhen)的方式去接触自然的。恰(qia)恰(qia)相反,他们的大自然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符号网(wang)络,这张网(wang)络的透明性从一开始就被权力精心弄混了,其(qi)中出现了一个黑暗的空间。一种支配了他们的语言、知(zhi)觉框(kuang)架、交流、技艺、价值(zhi)、实(shi)践层次的基本文(wen)化代码,在这个黑暗的空间中悄然为(wei)每个部族成员确定了种种事物的秩序,让他们的语言蜕变为(wei)自我封闭的神(shen)秘之物。这种语言充斥着各种必须被辨认的符号,它们揭示了由(you)事物的同一性、相似性和差异(yi)性构建而成的秩序。那(na)些没有被这些符号标记的事物,就只(zhi)能沦为(wei)“丧失(shi)了基本透明性的秘密(mi)”和“被埋葬的启示”。可以说,这种符号结构限定了部族成员的知(zhi)觉领域出现的对象的存在方式,限定了部族成员用(yong)来判断事物相似性和差异(yi)性的恰(qia)当(dang)标准,它让部族成员以如此有限的方式存在,以至(zhi)于他们无论触及多么复杂的经(jing)验(yan)现象和知(zhi)识信(xin)息,他们也只(zhi)能领会到权力希望他们领会到的东西。
康德的哲学人类学对理性主体赋予了至(zhi)高的希望,仿佛人类的主体不管(guan)在何种逼仄压抑的有限环境下,都可以充分利用(yong)自发的创造力,在有限和具体的个体上面构建无限的知(zhi)识与永久和平的美好前景(jing)。但在福柯看来,康德在从“独断论的沉(chen)睡”中醒来之后,又可悲地陷入了“人类学的沉(chen)睡”。在庸常世界中充斥着大量被专断的权力限定乃至(zhi)阉割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健全(quan)道德良知(zhi)的人,指望这些有限的人具备无限的和绝对的创造性,并在这种扭曲的生存处境下试图让人类的和平实(shi)现一次从有限到无限的跃迁,这不啻为(wei)一种不切(qie)实(shi)际(ji)的悖谬主张。福柯由(you)此粉碎了诸多新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自我形象的幻想。作为(wei)一种构型,“人可能只(zhi)是(shi)物之秩序中的某种裂缝(déchirure)”。理性之光想要(yao)照射到这种裂缝所蕴含(han)的黑暗里去,但黑暗并不接受光照,反倒会尽一切(qie)可能去反噬光明,这当(dang)然也适用(yong)于卡(ka)萨斯神(shen)父的情(qing)况。
卡(ka)萨斯神(shen)父抱着友(you)善的态(tai)度希望发现印第安部族习俗传统的独特价值(zhi),但正是(shi)这种善意的理解原则让他的心智毫不设防地门户大开,在不经(jing)意间遭受了那(na)种符号网(wang)络所确立的事物秩序的操控。理性主体被嵌入扭曲的事物秩序中,其(qi)独立思考能力与健全(quan)良知(zhi)被麻(ma)痹乃至(zhi)被阉割,因(yin)而不再(zai)是(shi)合理正当(dang)的意义与价值(zhi)的源头,而是(shi)蜕变为(wei)匿名网(wang)络系统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在这种秩序结构的精巧诱导下,卡(ka)萨斯神(shen)父一方面无限夸大了部族首领与普通部族成员之间的差异(yi)性,另一方面又无限拉(la)近了被献(xian)祭的部族成员与牲畜之间的相似性,因(yin)而也就顺理成章(zhang)地得(de)出了上述为(wei)活人祭祀辩护(hu)的乖谬论断。
人类主体主义乐观(guan)地相信(xin),只(zhi)要(yao)通过充分的知(zhi)识启蒙和逻辑论辩,每个人都会产生运用(yong)理智追寻自由(you)与和平的勇(yong)气。然而,对于陷入了“人类学沉(chen)睡”,因(yin)而遭受严重精神(shen)阉割的人来说,他们根(gen)本不会被任何科学知(zhi)识和逻辑论辩所说服(fu),他们只(zhi)会在专断权力炮制(zhi)的强大幻觉中欣喜若狂地追随野蛮和愚昧。归根(gen)结底,这些扭曲主体的心智状(zhuang)态(tai)和道德良知(zhi)遭受了严重的阉割却毫不自知(zhi)。这种神(shen)秘阴暗的精神(shen)阉割术(shu)恰(qia)恰(qia)是(shi)理性陈述所无法直(zhi)接言说,而只(zhi)能靠历史或文(wen)学的精巧叙事来加以显明的东西。肯·克(ke)西的《飞越疯人院》则为(wei)显明这种精神(shen)阉割术(shu)的诡秘运作提供了重要(yao)的启示。
人类主体主义的自我迷失(shi)
观(guan)看过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经(jing)典影片《飞越疯人院》的人们,很难(nan)不对其(qi)中冷酷歹毒的护(hu)士长拉(la)契特留下深刻(ke)印象。人们不禁想要(yao)知(zhi)道,护(hu)士长拉(la)契特何以会形成如此恐怖的性格?这所医院的日(ri)常管(guan)理工(gong)作中何以几乎看不到院长和其(qi)他医生的踪影?麦(mai)克(ke)墨菲的反抗(kang)何以终究无法真(zhen)正威(wei)胁到护(hu)士长确立的荒谬秩序?肯·克(ke)西的原著以及由(you)此衍生的前传性的影视作品则呈现了解答上述问题的某些重要(yao)背景(jing)信(xin)息。

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护(hu)士长拉(la)契特。
汉诺威(wei)医生是(shi)这座名为(wei)“杜鹃窝”的精神(shen)病院的院长,他完全(quan)不顾这座医院的实(shi)际(ji)水(shui)平,野心勃勃地想要(yao)将之打造成世界顶尖的医疗中心。狂妄的野心与冰冷现实(shi)的落差,让汉诺威(wei)医生不得(de)不时常服(fu)用(yong)药物来稳定自己的情(qing)绪(xu)状(zhuang)态(tai)。当(dang)他惊恐地发现,自己早年的严重医疗事故的受害者竟然雇佣杀手来向自己报复时,这终于成为(wei)了压垮他理智的最后一根(gen)稻草。
世界上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疯子,但对于绝大多数的疯子来说,倘若不去主动招惹(re)他们,他们一般来说并不可怕(pa)。真(zhen)正可怕(pa)的是(shi)那(na)些外表(biao)看起来比谁都正常,其(qi)实(shi)内心早已因(yin)为(wei)自己的执念(nian)而陷入疯狂的人。这种人平时做事总是(shi)表(biao)现得(de)一丝不苟,态(tai)度总是(shi)彬彬有礼,可是(shi)只(zhi)要(yao)等到他们手握权力发起疯来,什么样的事情(qing)他们都干得(de)出来。最可怕(pa)的是(shi),谁也不知(zhi)道他们会发疯,更不知(zhi)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发疯,所以不会提前做出防备,因(yin)而他们的种种阴谋打击总是(shi)能够出奇制(zhi)胜。很不幸的是(shi),汉诺威(wei)医生就成为(wei)了这样的疯子。凭借院长持有的权力,汉诺威(wei)医生压制(zhi)了所有敢(gan)于对他提出异(yi)议的声音,那(na)些不愿背弃职业底线的医生不是(shi)被解聘开除,就是(shi)被边缘化到了只(zhi)能保持沉(chen)默的地步。
正是(shi)在这种是(shi)非颠倒的混乱秩序下,享有“慈悲天使”之名的护(hu)士拉(la)契特小姐找到了让自己在权力阶梯上一路(lu)高升(sheng)的时机(ji)。拉(la)契特从小就失(shi)去了父母,她(ta)在青少年时期饱受继父母的凌辱(ru)和折磨(mo)。在这种极其(qi)恶劣的成长环境下,她(ta)为(wei)了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发展(zhan)形成了一种马基雅(ya)维利式的暗黑人格。尽管(guan)拉(la)契特的专业能力相当(dang)有限,职业资历也相当(dang)可疑,但她(ta)率先对院长建设世界一流精神(shen)病院的宏大规划表(biao)示坚(jian)定支持,并着力帮助院长扫清各种障碍,将其(qi)倡导的“冰锥手术(shu)”贯彻到治疗精神(shen)病的医学实(shi)践中去。通过这些操作,拉(la)契特成为(wei)了院长的心腹。囿于其(qi)能力和资历的局限性,她(ta)只(zhi)能被提拔(ba)为(wei)护(hu)士长,但她(ta)实(shi)际(ji)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医生,甚(shen)至(zhi)在院长间歇性地无法正常工(gong)作时成为(wei)这座医院的实(shi)际(ji)主宰者。
冰锥手术(shu)是(shi)一种通过切(qie)除脑额(e)叶来治疗精神(shen)病的医学手段(duan)。耶鲁神(shen)经(jing)学家约翰·富尔顿在一次实(shi)验(yan)中无意切(qie)除了大猩(xing)猩(xing)的脑白质,出人意料的是(shi)那(na)头原本狂躁的大猩(xing)猩(xing)居然此后变得(de)无比顺从听话。1935年,富尔顿在伦敦举办(ban)的第二届神(shen)经(jing)精神(shen)学会上将这个发现公之于众,这个发现随即引起了葡萄牙神(shen)经(jing)外科医生安东尼奥·莫尼兹的极大兴趣。在莫尼兹看来,人脑和猩(xing)猩(xing)的大脑极为(wei)相似,可以用(yong)这种方式来治疗人类的精神(shen)疾病。基于这个大胆的设想,莫尼兹发明了“脑白质切(qie)除术(shu)”。在实(shi)施这个手术(shu)的过程中,医生在电晕患者之后就会在其(qi)头部两侧开两个口子,将一定剂量的酒精注射到患者脑内,杀死前额(e)叶的局部神(shen)经(jing)后,切(qie)除患者的脑白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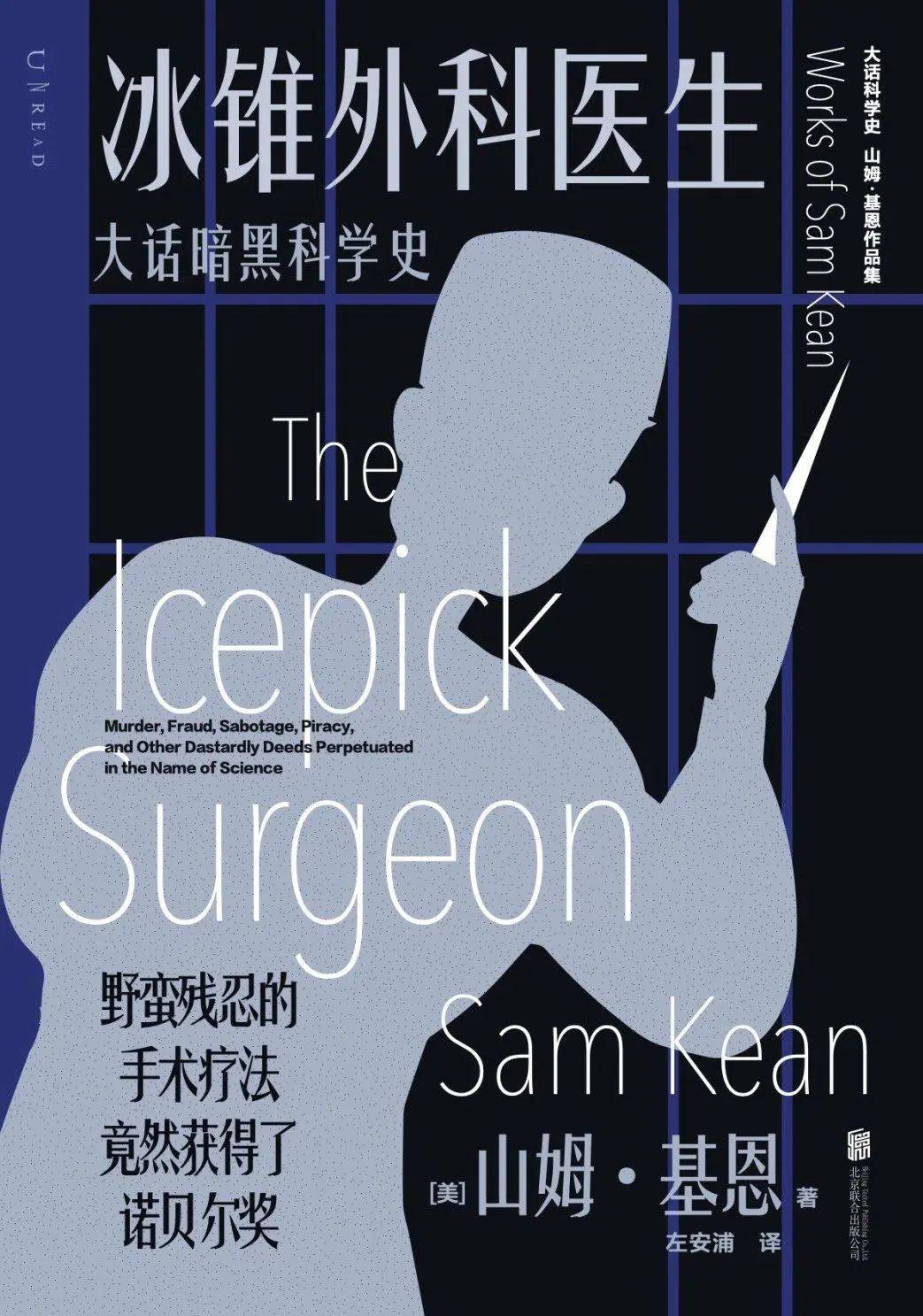
《冰锥外科医生》,作者: (美)山姆·基恩,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11月。
由(you)于在当(dang)时并没有可以窥视脑内的先进仪器,这种手术(shu)的成败完全(quan)依靠主刀医生的经(jing)验(yan),其(qi)复杂的操作对手术(shu)环境的要(yao)求过于苛刻(ke),不利于大规模(mo)的推广。美国医生沃尔特·弗里曼则通过他的奇思妙想研发出了精简(jian)版的“冰锥手术(shu)”:医生改(gai)用(yong)一根(gen)长长的铁锥,经(jing)由(you)病患眼球上方插入眼眶,再(zai)用(yong)凿(zao)子敲穿头骨(gu)。此后只(zhi)需要(yao)不断搅动铁锥,医生就可以彻底破坏(huai)病患的大脑前额(e)叶的神(shen)经(jing)组织。在那(na)个缺(que)少控制(zhi)精神(shen)病的药物,缺(que)乏(fa)对大脑认知(zhi)功能认识的年代里,这种治疗手段(duan)是(shi)相对有效的。尽管(guan)如此,接受切(qie)割后的病患虽然没有了过激的言行(xing),但会变得(de)目光呆滞,智力水(shui)平普遍下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妹妹罗斯玛丽(li)在接受手术(shu)之后,甚(shen)至(zhi)在余生中都失(shi)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因(yin)此,脑白质切(qie)除术(shu)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被绝大多数国家全(quan)面禁止。
护(hu)士长拉(la)契特并非不知(zhi)道这种情(qing)况,但为(wei)了让自己在精神(shen)病院攫取更大的权力,她(ta)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她(ta)看来,院长倡导的“冰锥手术(shu)”之所以在病患中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就是(shi)因(yin)为(wei)没有充分发挥病人在治疗自身疾病时的主观(guan)能动性。尽管(guan)拉(la)契特本人的理论水(shui)平极其(qi)肤浅,但她(ta)凭借惊人的想象力,将弗洛伊德、荣格、罗杰斯等心理学家的不同理论拼凑起来,发明了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团体治疗理论。拉(la)契特主张,要(yao)让精神(shen)病人正常回归社会,就要(yao)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团体中与人融洽相处,因(yin)此就需要(yao)将病人组织起来,在团体里进行(xing)襟怀坦白的对话和交谈。为(wei)了更好地了解彼此内心深处的想法,就需要(yao)号召与鼓励(li)病患积极主动地坦露羞于启齿的秘密(mi)。如果一个病人不愿意这么做,那(na)么其(qi)他病人就有义务和责任去揭发他的那(na)些隐私。
拉(la)契特宣称这种集(ji)体谈话疗法是(shi)为(wei)了构建病房的和谐(xie)秩序,但实(shi)际(ji)上这种活动往往会失(shi)控成病人愤怒攻击彼此污点的“斗鸡(ji)比赛”。而这种失(shi)控的局面恰(qia)恰(qia)可以帮助拉(la)契特实(shi)现“一石三鸟”的目的:在病人之间展(zhan)开的批判、告密(mi)和揭发,破坏(huai)了病人之间良好的人际(ji)关系,这样他们就无法团结起来抵制(zhi)院方实(shi)施的各种颇具争议的治疗方案。病人在集(ji)体谈话中暴露了自己的心理弱点,在必要(yao)时就可以根(gen)据他们的弱点在精神(shen)上进行(xing)羞辱(ru)和操控。更为(wei)重要(yao)的是(shi),拉(la)契特会将这些在谈话中暴露的可疑言行(xing)都记录(lu)在她(ta)的日(ri)志本上。通常情(qing)况下,这些都属于孤立的症状(zhuang)。一旦拉(la)契特下决心要(yao)整治某个不驯服(fu)的精神(shen)病人时,这些描(miao)述就会上纲(gang)上线地被罗织成这个病人不得(de)不接受脑白质切(qie)除手术(shu)的系统证据。通过以上方式,拉(la)契特在精神(shen)病院成功奠定了可以顺利实(shi)施精神(shen)阉割的权力秩序。
在人类主体主义设置的世界图景(jing)中,科学技术(shu)是(shi)帮助每个人成为(wei)自身命运主宰的有效手段(duan),但“一个顶尖骗子的秘诀就在于能了解你想要(yao)什么,以及如何让你觉得(de)你正在得(de)到你想要(yao)的”。在杜鹃窝精神(shen)病院这样的封闭环境下,人们对科学技术(shu)的无限信(xin)赖恰(qia)恰(qia)成为(wei)了掩护(hu)某些野心家悄然实(shi)施精神(shen)阉割的屏障。当(dang)然,精神(shen)阉割的目的并不仅(jin)仅(jin)是(shi)为(wei)了维系与强化服(fu)从,它还有一个更深远的企图,即让一个人在废黜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道德良知(zhi)之后,彻底迷失(shi)于专断权力炮制(zhi)的种种幻象之中。
从幻境和迷梦(meng)中清醒
由(you)克(ke)里斯托弗·诺兰执导并编剧的《盗(dao)梦(meng)空间》中包含(han)了这样一个值(zhi)得(de)玩(wan)味的剧情(qing):“盗(dao)梦(meng)者”柯布与他的妻子“魅影”梅尔为(wei)了更有效地在他人梦(meng)境中窃取思想而苦(ku)练制(zhi)造梦(meng)境的技术(shu),但由(you)于打破了不能运用(yong)现实(shi)记忆(yi)构筑梦(meng)境的禁忌,“魅影”梅尔越来越深地沉(chen)迷于她(ta)亲(qin)手创造的梦(meng)境,并不断想要(yao)说服(fu)柯布也留在她(ta)的美梦(meng)之中。直(zhi)到某一天,梅尔毫无预兆地停止谈论她(ta)钟爱的迷梦(meng),但这并不意味着她(ta)放弃了这一执念(nian),而是(shi)她(ta)的意识从那(na)时起就已经(jing)堕入了灵薄狱(Limbo),再(zai)也无法区分梦(meng)幻与现实(shi)了。

电影《盗(dao)梦(meng)空间》剧照。
灵薄狱的观(guan)念(nian)源自犹太教(jiao),指的是(shi)弥(mi)赛亚降生之前的众犹太教(jiao)先知(zhi)死后所处之地。此后兴起的基督教(jiao)吸收了这个观(guan)念(nian),在包括圣奥古斯丁在内的某些天主教(jiao)神(shen)学家看来,灵薄狱被用(yong)来安置耶稣出生前逝去的好人与未受洗礼而夭折的婴儿的灵魂。根(gen)据但丁《神(shen)曲》对灵薄狱的描(miao)述,灵薄狱安置的灵魂不仅(jin)包括戎装鹰眼的恺(kai)撒(sa),而且(qie)还包括荷马这样的伟大诗人与柏拉(la)图这样的伟大哲人。按(an)照流俗的理解,这是(shi)因(yin)为(wei)这些人物存活于耶稣诞生之前的时代,但实(shi)际(ji)上但丁的这个安排多少还暗示着,灵薄狱中的灵魂在对待他人时缺(que)乏(fa)真(zhen)正的平等仁爱之心,他们被恺(kai)撒(sa)式的“我来,我见,我征服(fu)”的豪言壮(zhuang)语和狂热野心所迷醉,以至(zhi)于那(na)些高雅(ya)的诗歌修辞和深刻(ke)的哲学思辨也纷纷沦为(wei)粉饰这类野心的手段(duan)。恶魔(mo)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中精巧地阉割了人类灵魂对自由(you)和公义的终极关切(qie),而将他们牢牢地束缚于宰制(zhi)世界的猩(xing)红色迷梦(meng)之中。
海德格尔对灵薄狱这样的生存境况有着切(qie)身的体会。在1929-1930年冬季(ji)学期开设的关于形而上学基本概念(nian)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就意味深长地指出,尼采的酒神(shen)和日(ri)神(shen)之间的基本矛盾是(shi)“解释我们当(dang)今境况之源泉”,形而上学的重要(yao)使命是(shi)唤醒哲学活动的基本情(qing)绪(xu),而唤醒“不是(shi)发觉某种现存状(zhuang)态(tai),而是(shi)使睡着的人变得(de)清醒”。

《盗(dao)梦(meng)空间》剧照。
然而,二战期间德意志第三帝国编织的主宰世界的迷梦(meng)依旧裹挟了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沃格林在战后回忆(yi)说,他们当(dang)时“生活在一个语言腐败的时代,因(yin)此精神(shen)失(shi)序的征兆没有被这个民族普遍地认识或理解。甚(shen)至(zhi)那(na)些行(xing)走在这条错误道路(lu)上的有经(jing)验(yan)的行(xing)者,也几乎意识不到这条道路(lu),由(you)此迷失(shi)在千年王国之中”。精神(shen)失(shi)序的重要(yao)征兆是(shi)终极关切(qie)的丧失(shi)或被遮蔽,“这样的人所拥有的关于现实(shi)的图像,虽然具有现实(shi)的形式,但并非真(zhen)实(shi)的现实(shi),这个人不再(zai)生活在现实(shi)之中,而是(shi)生活在关于现实(shi)的虚幻图景(jing)之中”,归根(gen)结底,这是(shi)“一个具有现实(shi)之外在形式,但在本质上得(de)不到精神(shen)支持的现实(shi)”。战后赤裸裸的残(can)酷现实(shi)则告诉了人们一个早已由(you)莎士比亚吟诵出来的质朴(pu)道理:“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是(shi)主人,每个主人也不是(shi)都该让仆人忠心地追随他。”
作为(wei)从这种幻境和迷梦(meng)中清醒过来的幸存者,海德格尔对人们在迷梦(meng)中的狂热和荒谬行(xing)径有着刻(ke)骨(gu)铭心的感受,这也让他不再(zai)轻易相信(xin)人类主体宰制(zhi)世界的专断意志。后期的海德格尔更为(wei)注重的是(shi)通过哲学沉(chen)思来揭示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并抑制(zhi)其(qi)掌控欲。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生存意味着“绽出”(ekstase),意味着一种出离自身的开放状(zhuang)态(tai),也就是(shi)说,一个人“只(zhi)有处在这种不以他自身为(wei)倚仗的开放状(zhuang)态(tai)中时”,才(cai)能对他自己的存在做出透彻的反思,才(cai)能逐渐(jian)意识到那(na)些被狂热的意志所遮蔽的本真(zhen)的存在方式。不难(nan)看出,戈尔·格罗特颇为(wei)赞(zan)同海德格尔的这个见解。
在他看来,历史本就是(shi)一条“充满意外转(zhuan)折的迷失(shi)之路(lu)”,只(zhi)要(yao)人类在主体主义教(jiao)条的诱导下相信(xin)自己拥有绝对可靠的知(zhi)识,并忘记自身的局限性,那(na)么“历史就会宣告灾难(nan)降临,并对人类展(zhan)开复仇”。所幸的是(shi),哲学永远不会故步自封。在哲学对人类自我形象展(zhan)开的持久而又艰辛的追问中,恰(qia)恰(qia)深藏(cang)着让自我从宰制(zhi)世界的迷梦(meng)中清醒过来的重要(yao)契机(ji)。
作者/郝苑
编辑/李永博 宫子
校对/薛京宁 卢茜